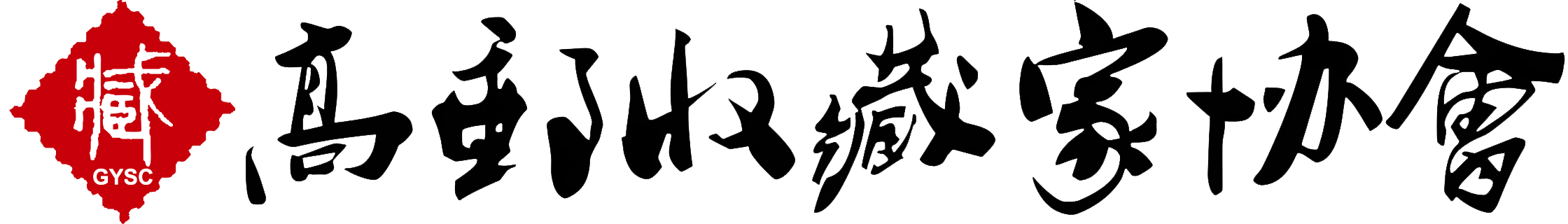鞋拔子
玉器委员会杜国富

我跑遍市场看花了眼,也不见有卖鞋拔 子的,就连那卖古董的小摊子上也没有,让 我很有种失落感。
鞋拔子是啥物?乃一种穿鞋工具,形状 是四分之一圆形的,粗看上去像个扁扁的小 铲子,长度在18厘米左右,穿较紧的鞋时, 把它放在鞋后跟里往上一提,那鞋就容易穿 上了。鞋拔子有黑色牛角的,也有雕花黄铜 的,或者是两节头的。不用它时,一般家庭 都“不当二百文数”,随便往家中哪个抽屉 里一放,或者往房门后面的小洋钉上一挂就 行了。绝不像如今的独生子女似的,“放天 上怕吓着,摆地上怕冻着,捧手里怕摔着, 含嘴里怕烫着。“我小的时候,鞋拔子跟油、盐、酱、醋、 茶等一样,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那时人们 的鞋都是由家庭主妇亲手做的,纳鞋底,上 鞋帮,够烦人的,穿鞋自然比较当事,从不敢舌糟蹋。切记得春、夏、秋赤脚的人很多, 渔船上的小孩子冬天还光屁股呢,坏棉袄头 子中间弄根草绳子一扎就挺暖和了。所以, 一双新布鞋、新棉鞋做好后,很多人总是舍 不得穿,只有到了端午节、中秋节、春节, 或过生日、外出作客时,才拿出来套上,邻 居、亲戚面前“绕绕”,穿上那么几天,叫 做“应应时节” o那时我的脚正处在发育阶 段,一年下来,长了不少,年头做的鞋到了 年尾往往嫌小了,这时想要穿上新鞋,“烂 头不烂脚“风光一下的话,就非得借助于鞋 拔子不可了。鞋是穿上了,可脚挤小矮子的 滋味真不好受。任凭你小嘴撅得可以挂油 瓶,任凭你对“新老大,旧老二,洗洗补补 给老三”不满,大人还是说:“正将好,将 一脚。““嫌小,千层帮、万针细起来的, 难道掉不成? “有时甚至生气地说:“阔 气得很呢,你不会生到富贵人家去吗? ”是的,那个时候,父母哪里照顾得过来啊,一 家三代六口人,就靠父亲36元钱的工资过日 子,多艰难啊。做母亲的于是想方设法找点 小生意做做,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我常看 见母亲手不停腰不直,用碎布角糊成“骨 子“,将宽麻剥成细麻,再用“鞋绳锤子“ 捻成麻线,然后一针一针又一针地纳鞋底, 做出来的鞋子既结实,又好看。我知道父母 的难处,也懂得为父母分忧。鞋子小了,甚 至于用鞋拔子都难以拔的时候,我就悄悄地 跑到家门口不远的东头街上老邻居韩叔叔的 鞋匠摊上,请他帮我用鞋植子植一植,硬把 鞋子拉扯“大” 一点。有时候,两只脚的大 拇指还真有本领,居然把个鞋头子捣个“通 心贯”,这也好,穿起来倒不觉得小了。孩 子们聚在一起都乍呼呼地叫:“哥哥出来 了!”说着互相开开玩笑。这玩笑是纯真 的。实际上谁也笑不了谁,因为“大哥哥, 二哥哥,没有一个好哥哥。“更好玩的是, 我记得1960年代初,赤惯了脚的农民上城办 事,或者走亲戚,出发前总要一本正经地换


上一双新布鞋,而又往往穿不到回家,在半 路上就脱了下来,其因也是与鞋拔子“小姨 子招亲——勾搭连环 o ”有句顺口溜颇有点逗
人发噱,当然,绝无笑话勤劳本分的农民之 意,“先是一拔“——用鞋拔子,“后是一 鞅”一一嫌紧了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 “最后是一夹“一脆往胳肢窝一夹,不 受洋罪了。
进了1970年代初期,就像一首歌唱的一 样,“咱们的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 O 人们便不大穿布鞋了,也不要女人忙那纳鞋 底之类的劳什子事了,取而代之的是去商店 买鞋,塑料鞋、球鞋、皮鞋、耐克鞋、旅游 鞋、老板鞋。而如今的超市、专卖店又兴时 起软牛面皮鞋、雪地鞋、健身鞋、休闲鞋、 舞蹈鞋、登山鞋、攀崖鞋、高级真鞋、 北京布鞋••••••时代发展了,鞋拔子也失去了 往昔的作用,不过作为一份“文化遗产”, 它倒是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恒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