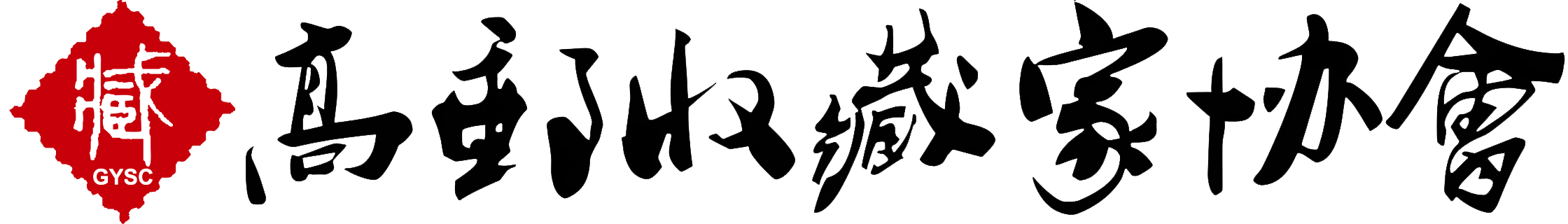怦然心动的“聚宝盆”
陶瓷杂项委员会马广元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
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
人们常说,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心灵的使者,更像是一段光阴的截屏。
近日好友于先生拍回来一件“宝贝”,很是兴奋,特地请我们去吃烤全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酒过三巡以后,于先生搬了一个大纸箱进来。一层一层拆开包装后,只见一个硕大的“潘趣碗”,静静地躺在盒子里。我和于先生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碗拿出来,轻轻地放在香案之上。
“太美了!”
“这么大的碗!”
敦厚大方,安静简单,让人立马浸透着它的美。一圈的人忙着拿着手机拍照。
“这么大个碗,下一碗阳春面的话,估计一大桌的人都吃不完。”同桌的一位朋友打趣道。
说句老实话,如此硕大,如此漂亮的碗,我也被震撼到了。尽管两年前,我也帮朋友买过一个达40公分大尺寸的,乾隆时期的粉彩九桃潘趣碗。(朋友是深圳的,当地富人们有一个习惯,用一个硕大的碗放在香案之上,讨个好口彩,称作为一聚宝盆。)
好友于先生拍此碗的当晚,私发图片给我看,而且一再和我讲:“这个碗大了,直径有40公分”,他非常喜欢。然而搞收藏的朋友们都知道,自古以来喜欢和拥有是两码事。圈里有句话:入我眼,即我所有。其实细细品味这句话,又透着些许的无奈。好东西又有谁不喜欢呢?关键是你要有经济基础做支撑呀!当晚从他志在必得的语气当中,我想还是决定给他泼点“冷水”。
“价格太高了,就没多大意思了”。拍卖玩的是数字,但是付出的可是真金白银呀。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陪他到处去淘宝。时至今日有40余年,所见和经手的东西不在少数,只是现在每年能够让自己眼前一亮,怦然心动的东西不多了。然而初识这个大碗的实物,还是被它彻底震撼到了。
此碗不仅体型硕大,难得的是如此大件品,器型相当规整。伊万里风格的通体釉下蓝配釉面金红通景山水纹饰。所绘画的青花山水上,康熙时期惯常使用的斧劈皴,表现得淋漓尽致。远的是淡淡的一抹青山,亦或是一叶孤帆。近处的楼阁庙宇,葱郁的山石树林,一切显得那么和谐,那么恬静,养眼更养心。如果说装饰的青花红彩表现的是型,那么流淌在其间的勾勒点点金描,则是情感的灵,让器物显得端庄又富有贵气,不失为外销瓷中的一件精品。
“潘趣碗”也被称为“潘趣酒碗”,由英文Punch音译而来,最初是由水手和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带到了欧洲。其主要功能是盛放酒、糖、柠檬、水、茶或者香料而调配而成的一种低酒精度的果酒,用于在节日庆典和聚会上饮用。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我们对它了解的不是太多,一般都在揣测,这么大的碗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欧洲贵族家庭中的长辈们,常常通过分发大碗里面的酒,来表达盛情,以及慈爱和威严,因而对此大碗崇敬有加。故此“潘趣酒碗”也大量出现在西方的绘画作品当中。
印象中以釉下青花,辅以矾红鲜明色彩的组合,勾以金色面釉,以日本九州港口伊万
里命名的日本伊万里瓷多采用,亦深受欧洲人的喜爱,获得众多的贵族私人收藏。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在18世纪初的时候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
如此这般美的“潘趣酒碗,”生机勃勃地立在那,口沿的两三处爆釉,仿佛在倾诉着自己,近三百年来流转的艰辛,让人惊叹也更让人惊艳。
我总是以为在我不够专业的视野里,瓷器是憔悴的、孤独的,也总是有着裂纹,惊釉和飞皮等瑕疵,仿佛不残不破,就不足以说明它们的身世。当然也曾见过五彩镏金,镂空繁复,极尽奢华的藏品。暮景千山雪,冬寒百尺楼。历史的话语总是太过于沉重,艺术在博天子和美人一笑中流传。而如今我们更多的人,只是看中那一笑的传说罢了。